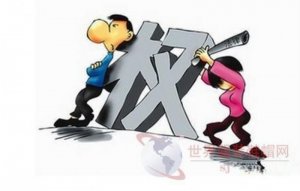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九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15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九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2016年5月3印 阅读《上学记》和《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何兆武和汪子嵩对前尘往事,流淌在字里行间,抱着一个反省的态度。比如说,殷福生同学在西南联大站在党国立场,让何兆武和汪子
|
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九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2016年5月3印 阅读《上学记》和《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何兆武和汪子嵩对前尘往事,流淌在字里行间,抱着一个反省的态度。比如说,殷福生同学在西南联大站在党国立场,让何兆武和汪子嵩忍受不了,给殷福生扣上“反动”和“落伍”的帽子,一点都不冤枉。至于殷福生到了台湾之后,走胡适先生的道路,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成为戒严时期温暖无数知识分子的“燃灯者”,何兆武和汪子嵩回首往事,特别提到殷福生,以为以前对这位同学的看法是有偏见的,不公允的。赵俪生一辈子,都有点心绪难平,疙疙瘩瘩,但,赵俪生对“左倾”也是有着基本的反省的。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来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还有一种学友——许渊冲,懂得感恩,特别厚道,西南联大的师生,凡是回忆到的,流淌着一种美好的感情。至于张世英先生,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均衡,老辈学人回忆录,何兆武、汪子嵩、赵俪生、许渊冲、张世英,都很有意思,流淌着回忆者的真性情。学界中的海外华人,既然在世界舞台上驰骋,描绘中国学术地图,就不愿意再让这些“巨星”憋屈在中国大陆这一亩三分地;另一方面,也许还有一个因素,海外华人学者,在欧美学界,遇到一个很大的天花板,最后,多多少少有一种学术上的回归,在海外治中国学问,徐贲先生,这种接中国地气的学人,到底还是罕见。1978年以前,中国学界有近三十年时间,与其说是闭门造车,不如说是政治挤压学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学者,以其先天的优势,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信使,激活了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范式,对新时期的学术研究,还是很有裨益。但,打开国门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学人不自信,海外华人学者也给大陆学人带来了不少“洋片汤”,中国大陆学人以前所信奉的菩萨,似乎都不顶用了,换不上洋菩萨,摆上一尊海外华人菩萨,也好。有些华人学者内心深处,有着相对深刻的自觉,在欧美学界以中国为研究范围,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欧美学界主流,至少不以中国为主要研究范围,这是可以确定的。华人学者研究欧美,不管语言多么过关,也有一个是否接地气的问题。华人学者真正想做一流的研究,至少要抛弃“胡适类型”,换上“马寅初类型”吧!确实,欧美学界保存、搜集了大量中国史料,而且那里的大学拥有阅读自由的权利,但,海外华人学者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身在万水千山之外,这种对中国的距离感,既有可能客观看待中国文明,也有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失去一种了解之同情。海外赤子,回到故乡,按理说“近乡情更怯”才对,但,何炳棣先生,一辈子生活在成功之中的史学家,不会不知道《读史阅世六十年》的阅读者多为相亲们这一事实,依然以一种很高傲的姿态,回首往事,作为简体版出版方的——中华书局,应该以一贯的严谨,去帮助这位史学家裁节自己的感情,反倒任这位史学家在相亲面前自负到“得瑟”的程度,还在那里点赞:这是一位真性情的真学者,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何炳棣这种“自负”在这本自称学术性的传记之中,充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各个段落。何寿权先生在四十八时,才有了何炳棣这个独子,“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何炳棣将自己的秉性追溯到和父亲之间的年龄差距,在清华遇到潘光旦先生,潘先生就会有一番真正符合科学的解释。《读史阅世六十年》阅读之中,让我感喟:何炳棣真是一位史学家吗?这是一位史学家的传记吗?何寿权先生跟何炳棣说及:“你祖父寿至八十三,祖母寿至八十七,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寿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何炳棣的父亲只是一位前清的廪生,每年最多发四两廪饩银而已。何炳棣父亲倒是一位开明人士,因为在金华老家毁庙兴学,不为乡里所容,离家北上,最后落脚天津,何寿权先生是否脾气也很急,也很大,何炳棣并没有直接谈及,而是通过一位堂哥——何炳松之口,“我们上一辈兄弟四人之中,以三叔为最有才,性格也以他为最倔强。”在何炳棣眼中,自己父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何寿权先生,也确实倔强,当年毁庙兴学之举,得罪了父老乡亲,启程之前何寿权先生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孩子何炳棣阴历十岁那年,这位前清廪生背井离乡多年之后,因为梦见父母,才想起来按生日、忌日祭祀父母。何炳棣“自负”,还来自有点意思的家族。姨父俞星槎在保定陆军学校学习时,与同宿舍的白崇禧友善,成为新桂系重要的幕僚,曾担任过国防大学中将教育长。堂哥何炳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暨南大学校长。“阿松哥”长何炳松二十七岁,与何炳棣一家,往来并不多。以至于1936年春,正在清华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何炳松,要不是潘光旦教务长的细致,堂哥何炳松走到身边,即使何炳棣看到了也不大认识。当时已经担任暨南大学校长一年的何炳松先生,来到清华大学观摩,在何炳棣嘴里,就变成了“北平教育考察团”。何炳棣回忆:一天下午,看见教务长潘仲昂(光旦)先生陪着一位修长、潇洒、平头,身着灰呢长袍,手持高级烟嘴而不吸的“绅士型”的中年学者,满满地走向我的面前。潘先生说:“你哥来了,你还不知道!”堂侄何德奎是三四十年代何氏家族的一位中流砥柱。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同窗有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学成归国,曾任教于大同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工部局首位会办,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是钱大钧的得力助手。何德奎夫人杨闰康,岳丈杨荫杭,妻妹杨季康,妻妹夫钱钟书。以上这些亲戚,都能引起何炳棣的自豪以至于自负。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与何炳松的对照着阅读,也许会很有意思。季羡林先生会哭穷,山东在中国很穷,临清在山东很穷,自己的村庄在临清又是最穷的,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为山东以至于中国的贫困户了。这种印象很是深刻。某种程度上,季羡林印象中的贫困,打上了一生的底子,异日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忘本,这决定了季羡林待人接物的朴素。何炳棣说父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这一句话,非常意味深长。清华大学出身特殊,袁项城也很喜欢,清华为此专门给袁项城的后代预备了一个绿色通道——袁氏后裔生。当然,袁氏后裔也不都是非上清华不可,袁克文之子——袁家骝就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清华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不少,大家印象中那些“二代”朴素、低调,待人接物,很有礼数,显示了世家子一点好家风。何炳棣父亲怀才不遇,也算得上家道中衰,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不屈服,或者抗争的性格,鼓励孩子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何炳棣没有得到堂侄——何德奎的支助,在水木清华,极有可能与赵俪生、王瑶、魏臻一同学一起成为“革命左派”。何炳棣父亲的怀才不遇,并没有让何炳棣往左派方面走,何德奎每年二百块大洋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管何炳棣本人是否认可。何炳棣一生都在立志,不论早岁还是晚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史阅世六十年》不妨当做一首诗,而不是传记。即使诗人,经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也应在晚年变得恢宏大度,至少有一点宽容,但,那样的话,就不是何炳棣了,而是另外一个人了。何炳松为了证明自己一生选择之正确,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何炳棣就把自己与清华大学结缘,追溯到还是九岁小学生的时候。父亲虽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明白白地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早在1926年冬一个日丽风静的星期天下午,他带我去八里台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那宽敞画出跑道的田径场、秀山堂、思源堂等西式的建筑,真开了系小学生的眼界。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长大要不要来这里读大学。我说当然想来读。他面容马上变得很严肃,指出南开之有名是因为中学办得好。办大学很费钱,南开大学是新开办的,底子还不够厚。他紧接着说,他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样留学;而“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我问父亲怎样才能出洋。他说本来像炳松哥和阿奎(德奎)都是考取浙江省和教育部的官费留美的,现在浙江已经没有官费留学了;本来清华学堂毕业个个都派出洋,听说清华已准备改成大学,改成大学以后毕业生恐怕不能个个出洋了。出洋是越来越难了。看来还是只有多用功先考进清华大学再说,反正清华的学生考取留学的机会要比别的大学学生多一些。于是我从九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更大的志愿。(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9页)这时何炳棣入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不到两年,开蒙不久,何寿权就要在南开大学跟小孩子立志,未免有些拔苗助长吧!何炳棣为什么不把自己年龄说的再小一些,比如1925年以前,岂不是更显得何炳棣早慧?那样,怕是没人信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长大以后,何炳棣成为清华的粉丝,大有非清华不上的气势。问题是1933年何炳棣高考失利,当年没有被清华大学录取,既然,九岁就已经抱定了清华的决心,没有考上,就应该进行“二战”,事实上,何炳棣并没有在家复读,而是来到青岛,入读山东大学。再则,一位前清廪生,四十八岁老来得子,舐犊情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竟然给八九岁的小孩子灌输,不能留洋就一辈子受气的观念,一方面可以说,何寿权先生有开眼看世界的眼光,另一方面,也太有点不自重了吧!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点线索,何炳棣的自负、自傲,从何而来!何老爷子这种家教,确实凤毛麟角。这番话,对还提的何炳棣似乎很受用,何炳棣考到清华,也出洋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过,似乎有点过了,助长了“以高等华人自居”的一种心态。最有意思的是,何炳棣的尊人,未卜先知的本领。南开中学办得好,这是众所周知、有口皆碑的,先有南开中学,后有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1926年冬天,何寿权先生带着独子——何炳棣在南开田径场立志时,南开仅仅是第七个年头。但,一所已经创办七年的大学,竟然比不过尚在改大之中的清华,岂不是匪夷所思!只能说,何寿权先生,做梦都盼着何炳棣出国,有朝一日,成为“海归”,镀金回国,才能扬名立万,否则,一辈子灰头土脸。此种情形,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不少见。何炳棣一生的成败,在此一举。何炳棣顺应时代潮流,功成名就,泰半得益于考取清华和出国留洋两大目标的实现。《读史阅世六十年》不惜笔墨,再三再四叙说这两件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了。前两日没有写作,一字一字敲出来《大学一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以通才教育为尚。但,现实生活之中,还是有所妥协,只能做到大学一年级不分系。以前聊过《“转弯”的哲学》,说的是张世英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最后转到哲学系,何兆武更有意思,大学四年,读了四个系,土木工程系—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何炳棣也有一个“转弯”,从化学转到历史。何炳棣怎么解释这个转变?还是追溯到1926年,尊人依照生日和忌日祭祖时,何寿权先生跟孩子的唠叨,何炳棣对此异常重视,以至在自传里,特别交代一笔: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何寿权先生简单随意给何炳棣聊一点国学,涉及到经史子集,只不过,零敲碎打而已。这种教育,大概比起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国学,还更多一些,但,中国学问的根底,还是差了好多,自负的何炳棣,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难能可贵了。接下来的说辞,就让人不打好理解了:必须郑重声明的是,以上概括性的回忆很容易给读者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先父自始即诱导我成为一个史学家。(《读史阅世六十年》第8页)多学科取向的种子,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史学家。以上这些,都是为何炳棣曾经选择化学做一种铺垫。大概只有这样说,才能维护何炳棣一个高大帅气的学术形象。何必呢?即使苦心维护,何炳棣也应该与好友杨振宁联系在一起。杨振宁要小何炳棣五岁,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清华,而是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入读的就是化学系,以此来论证,当时化学系是学术精英的不二之选。解释的力度,岂不更大!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的刘逸民先生,有识人之明,刘先生在三年级终了对何炳棣有一个总评,最后一句话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老先生在何炳棣八九岁,就能看出何炳棣最大的缺陷,不能与人和谐共处。何炳棣清华同级学友——赵俪生,也有这样的缺陷,但是,看过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特别是赵夫人高昭一的说明,对赵俪生产生一种同情之理解。何炳棣这种“葛”,就让人喜欢不起来了。何炳棣1928年到1932年,在南开读中学。整整四年,喜欢的老师也就一位——柳无忌的夫人——英语老师高蔼鸿,因为高老师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高老师嘉善人,十次口头考问全班,六七次总要先问——“吴彬第”(何炳棣嘉善读音)。还有一位令何炳棣印象深刻的老师——张伯苓先生的弟弟——张彭春。何炳棣说了一句——张彭春对发展话剧贡献甚大。接着就叙说自己怎么被南开开除的。事情的缘起,1932年秋天,《南开双周》内容越来越激烈,当时张伯苓先生不在天津,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召集《南开双周》编辑谈话,勒令停刊,激起公愤,南开同学召开大会,向校方表示强烈抗议。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抗者也不多见。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往往需要一个“憎恨”反抗的对象才能维持心理和行为的平衡。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仿西方某派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势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打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3——44页)何炳棣在中学和大学,有过一段社会活动家的生涯,初试身手,就以南开学潮的罪魁,当即被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开除,高蔼鸿老师求情也无济于事,何炳棣记恨了张彭春主任一辈子。以至于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都难以平息何炳棣心头之恨。还在那里诅咒,最“缺德”的是张彭春连转学证书都不发,逼得我在1933尿酸钠初在北平不得不假造一张转学证书,盖的是“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大方木制的假图章。(《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4页)这就不是性格和脾气所能解释的了,何炳棣漂流海外,一直在学府教书育人,与张彭春先生同在北美,要是有一天,何炳棣回首往事,化解了心中的怨恨,前往张彭春先生府上叙旧,聊聊人生的过往,岂不是现代学界的佳话!何炳棣之所以是南开学潮的罪魁,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作为一位阅读者,不大明白的是,《南开双周》越来越左,言论偏激,引起何炳棣内心不满,南开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先生勒令停刊,按理说,遂了何炳棣的意了呀!何炳棣应该高声叫好才是,怎么就闹起来了呢?大概,没有这件事,何炳棣也要闹一闹的。1933年,何炳棣备战清华大学失利,躲在家中复习,倔强的老父直面倔强的小儿,如此场景,令人悲怆。权衡之下,何炳棣来到青岛,步入山东大学,权且在此地潜伏吧!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一年,也很有意思。当时校长是赵太侔先生,萧规曹随,遵照前校长杨振声先生的兼容并包方针,才人之盛,粲然可观。闻一多、游国恩、萧涤非、梁实秋、洪深、老舍、沈从文、吴伯萧、王统照、丁西林、童第周、傅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何炳棣入读化学系,发现这里可能是全校最坚强的一个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傅鹰教授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一般学生难以接近。何炳棣说傅鹰教授是密歇根大学博士,据查,傅鹰先生毕业于密执安大学。山东大学外语系主任梁实秋先生,决定对大一新生进行外语水平甄别考试,何炳棣考第二名。有求益心的学友,对考试成绩,自然是在乎的,不过,在乎到何炳棣的程度,确实不多见。梁实秋先生最初担任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这是何炳棣考取山东大学之前的事情了。1931年、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学潮不断,闻一多和梁实秋,清华前后级学友,作为杨振声校长的左膀右臂,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闻一多和梁实秋锋芒毕露,迎着学潮上,受到学生担待,闻一多被视为法西斯蒂主义者,间或有少数学生喊出——打倒不学无术的闻一多!闻一多哪里受得了窝囊气,于1932年回到了水木清华。梁实秋是闻一多引荐给杨振声先生的,学校壁报上画着一只乌龟,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大名,两位见到后,苦笑不已。性情刚烈的闻一多离开了国立青岛大学,但,雍容的梁实秋,并没有与闻一多同进退,离开青岛大学这个是非之地,有情有趣的梁实秋,已将青岛视为人间仙境了。1932年杨振声先生去职,赵太侔先生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也就是说,1933年何炳棣到山东大学时,梁实秋依然担任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主任。何炳棣在山东大学遇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英语老师——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读史阅世六十年》第51页)诸葛殷同回忆:我辈在北京大学上学,节日常常分批去老师家问候起居。有一次彭燕韩学兄在金先生家忽问金先生:您以前结过婚没有?金先生说:曾与一美国女士同居过。彭兄说:金先生,你还干这种事!金先生有点生气,站起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彭兄吓得不辞而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理有固然——纪念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第6页)金岳霖先生如果有一个孩子,很多喜欢打探名人隐私的,绝对不会寂寞。金先生身上流淌的魏晋风度,老辈如金岳霖先生,襟怀坦白,也不会说为此事打掩护。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潜伏,很有收成,泰勒女士的辛劳没有白费,1934年何炳棣如愿以偿,与汪篯、魏蓁一、王瑶、居浩然、王永兴、杨志玖、任福善、吴承明、黄明信、赵俪生、黄诚、陈芳允、孔祥瑛、姚克广、王栻等二百八十六位同级学友一起迈进水木清华,有一位转入清华外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黄绍湘,与何炳棣在清华有深厚的渊源。1938年,何炳棣与汪篯、黄明信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前,1937年,黄绍湘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何炳棣在山东大学遇到汤腾汉和傅鹰先生,化学成绩有很大的提高,但,在水木清华,遇到了障碍。据何炳棣说,放弃的原因有三:一化学系宣布大一成绩达不到相当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二,张子高先生的教学作风,令何炳棣不满。三,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的几位同学,有着异常坚实的化学基础。何炳棣还说,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比照何炳棣所说,据查,1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共有16位同学毕业,1936年20位同学,1937年毕业24位,1938年何炳棣这一班级,有16位。全校最大的建筑——四层的化学馆,竟然容纳不了1931级到1934级总共也就百十来位学生!何炳棣从化学转入历史,民国时期,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以为怪。但,何炳棣要找出那么多理由。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三个,何炳棣的化学基础并不比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同学扎实,在班里面成绩落后,学了一年,也没有找到提高的办法,退而求其次,转入历史系了。如果何炳棣这么简洁明了,相信阅读者,依然会怀着最大的善意。试想当年找到了学习化学的办法,何炳棣会不会还在回忆录里埋怨张子高先生教学不得法?何炳棣的回忆录,颠覆了不少以往的印象。何炳棣回忆录中出现的一些老师,也出现在赵俪生的回忆录中,推想原因,何炳棣和赵俪生都是同年入学的同级学友,有些大课是一起上的,这样,就有了比较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老师,赵俪生不以为然的,何炳棣则奉若神明。大有亲不亲阶级分的味道。赵俪生对俞平伯,很不以为然,讲着讲着,就把自己的祖上抬出来了。何炳棣却说:俞先生虽兼重章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0页)比如刘崇鋐先生《西洋通史》,有些学友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好,但在何炳棣眼中,好的不得了,大概这门课程,鼓舞何炳棣从化学转入历史系。赵俪生回忆刘崇鋐和雷海宗,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推(资料),某某著,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赵俪生:《篱槿堂自序》第35页)再看何炳棣的回忆: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入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读史阅世六十年》第58页)同一门课,同一位先生,不同的是坐在下面的学友,一位赵俪生,一位何炳棣,都崇奉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一位是左翼,一位是右翼,听课的感受,竟然天差地别。依照高王凌先生的意见,不妨两说并列,各位阅读者,听一听两造之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民国历史而言,依然处在盲人摸象阶段,原因很简单,不合时宜之言,不合时宜之思,都是为读者所不喜的。刘崇鋐先生的《西洋通史》,有一次月考,何炳棣满以为准备很充分,却只得了89分,心高气傲的何氏,内心很是纠结,姚克广坐在右上方,得了91分,善意地对何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克广后来改名姚依林。大学三年,何炳棣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上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得到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四十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持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里的错误,但不知为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黄明信与何炳棣颇有渊源,为清华大学舍友。何炳棣具有一种颠覆性人格,大概何氏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恍然间,还以为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何炳棣作为一位出身清华的史学家,在回忆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时,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不承认陈寅恪先生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第二,要把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抬到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位置。且看何炳棣的说辞: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1980年何炳棣被访问时,对30年代清华历史系作了扼要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论断。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综合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看来何炳棣和清华同级学友王瑶有着同样的情结。不错,朱自清担任系主任长达16年,但弟子王瑶非要说朱自清领导清华中文系,对清华学派的产生贡献巨大,云云,云云。何炳棣则说,蒋廷黻先生1929——1935年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在清华历史学派中居于主导地位。一位文学史家,一位历史学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两位能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这种错误,是不会出现类似错误的。首先陈寅恪先生并不是一位精于考证的历史学家,精于考证,那是陈寅恪的好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历史学派的特征在释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里补说一点。何炳棣夸赞蒋廷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1935年,蒋廷黻来到清华的第六个年头,在历史系的改革告一段落,前往行政院任职。就以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程为例,看看燕京大学中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是否与何炳棣的说法吻合?1935年燕京大学历史系课程一览中国与东亚细亚, 《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顾颉刚)、《秦汉史》(邓之诚)、《魏晋南北朝史》(邓之诚)、《隋唐五代史》(邓之诚)、《宋辽金元史》(张星烺)、《明清史》(邓之诚)、《东北史地》(冯家升)、《中西交通史》(张星烺)、《中国之革新》(王克私)、《远东近世史》(洪煨莲)、《南洋史地》(张星烺)。十三门中,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邓之诚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和王克私《中国之革新》,六门课程,本学年不授,开设七门。东亚以外诸国史,《世界名人传记》、《南洋文化之基础》、《基督教史中之浪漫时期》、《革命时代之基督教史》、《上古至纪元前第四世纪》、《后期希腊与罗马》、《欧洲中世史,文艺复兴》、《独裁政治与欧洲革命》、《西洋史1871—1918》、《1871以来之西洋史》、《犹太人历史》、《罗马统治下之巴里斯登》、《古时至1603英国民主政治之发展史》、《1603以来英国民主政治之发展史》、《法国史》、《德国史》、《美国史》、《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经济史》、《基督教史》、《耶稣事迹考》。二十一门外史中开设十三门,有八门本学年不授。也就是说,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学年,国史开设七门,外史开设十三门。外史与国史的比例,将近二比一。中华书局却在出版社说明中特别强调:《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自传,他把自己一生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既是他个人“读史阅世”的学思历程,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丰富翔实,启人深思,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读史阅世六十年》,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禁不住心弛神往,才读到六十六页,就充斥着这么多妄说,是谁之过与? (2017年8月14日,书菜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