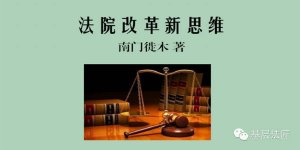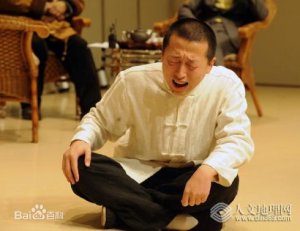|
公众广泛参与法律程序是让法律恢复活力的重要途经。 ——伯尔曼 问题出在了如何参与上。我一直认为舆论是监督政治特别是监督官僚的最好方式。如果从最广泛意义上讲,司法毫无疑问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但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定义监督。美国的民众抗议特朗普提名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特朗普的移民禁令;韩国民众在宪法法院门前支持或反对弹劾朴槿惠;香港4万人集会声援被判入狱的7名警察,在某种意义上讲均可视为对司法的“监督”和诉求的表达。因此,应当认为民众关注和关心司法的过程与结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即使在法治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不例外。 我们同样注意到,在上述事件中,美国、韩国或香港的法院与法官均未就其所做出的判决作出任何判决书以外的表态。换言之,法院将其全部的理据经由其判决向世人展示。毫无疑问,判决是法官关于案件的全部表达。质疑判决从本质上讲即是质疑作出裁判的法官与法院。显而易见,一个频频被质疑的司法系统,是不会有什么权威和地位的。然而,不论是美国、韩国或香港法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威望之高毋庸置疑。因此,一方面,不能认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院或法官经常为社会质疑与反对;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民众对判决的支持或反对即为对法院与法官的支持或反对。恰恰相反,民众的任何态度均是建立在对司法的信任与尊重之上。即便香港7警察案件后,人们在质疑7警察案判决结果的公正性时,从未忘记加上一句前缀,即“我们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毫无疑问,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正是构建司法权威的基石。 回到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贾敬龙案、赵春华案、于欢案三个著名的“公共”案例,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司法权威与尊严的基石正在不断地被冲击与破坏,且破坏的对象从基层法院一直延伸至最高法院。我常常在想这种对裁判结果,不论是生效裁判还是未生效裁判的质疑究竟是如何从个案演变成公共事件的,这种演变的过程又究竟与裁判本身有多少关联性。不知是否有人或者部门将上述案件作为某种社会学标本进行认真研究。在我看来,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贾敬龙案为例。当最高法院已经核准此案,仍有人在呼吁“刀下留人”,且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谈观点。难道这些不是在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可以完成的工作吗?诚然,辩护律师可以利用其人脉,聚集大量法学专家为其呐喊,但是这种呐喊不应当是由律师按照法律程序递交给审理案件的法院而不是利用媒体进行一边倒的呼吁吗?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尽管贾敬龙案在法律界引起广泛注意,但权威媒体和门户网站始终保持了克制与理性,并未参与此案的报道(我仅发现个别门户网站有个别报道,但很快被删除)。媒体的冷静与克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对社会的某种指引与规范,这种指引与规范指向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尊重与信任司法。如果说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最高法院便是最后屏障的最后保障。如果连最高法院已然作出的裁判都因顾忌所谓“言之凿凿”的文章或观点而放弃其权威,那么司法的尊严又能安于何处? 然而,赵春华案的一审判决和一审法院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份仅仅是量刑可能(仅仅是可能,这一量刑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幅度)稍微偏重的且尚未生效的判决,竟然会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赵春华上诉了。换句话说,媒体批判的对象——那份未生效的判决并没有对赵春华的实体权利产生任何影响。显而易见,不论媒体如何炒作,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赵春华已经犯罪,并且至少要适用缓刑。二审法院莫非没有能力审理这样一起案件?进一步的追问在于,即使赵春华上诉,这份一审判决也并未出现明显失当。人们或许常常认为自己掌握着所谓的常情、常识、常理,却忘记了法律本身就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与反映。气枪是枪支已经依法鉴定,持有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不能构成犯罪?我只能理解为少数人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裁判结果而巧妙地发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少数装作不明真相的所谓专家。 于欢案则是一起更加值得深入研究和予以高度重视的公共舆论事件。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以此案及类似案件为依据,制定出进一步规范律师与媒体、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制度,或许是中国司法乃至中国法治的幸事。我一直有一种隐忧,即当所谓的学者或时评人如果连判决都没看完或根本不愿意看完就急忙发表义正言辞的文章,是否应当受到必要的惩戒?当个别媒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杜撰学者的观点是否属于造谣?显然,尚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应该关心的问题。仿佛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已然不值得信任,仿佛审理中的案件已然可以随便干预,仿佛每一个看过新闻报道的人都可越过裁判文书教育法官。在我看来,这并非互相伤害,这是害人害己。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发动媒体资源的成本是什么,充分利用媒体批评司法的代价几何。事实上,并非每一起有研究价值的案件都有媒体关注,甚至可以认为,绝大多数有价值或有争议的案件,都是由法官通过审理和理论研究得以解决并将成果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推广。换句话说,中国的司法正是在这种平和理性的积累中得以不断进步。那么,为什么有的案件被媒体“发现”并高调报道呢?是这些案件真的很有争议吗?或许更多的情况恐怕仅仅是某些案件的利益相关者试图通过媒体来扭转对自身不利的结果,因而其需要付出的成本自不待言。于是,可以设想,案件的另一方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发动媒体,媒体均平等给予双方表达观点的权利,是不是才可真正称为平等论辩。进一步的追问是,基于对贫穷的被告人的公平对待,法院是否应该将每一起案件的判决书特别是一审判决书都要拿给媒体筛选后再拿到公共平台讨论评价?从媒体到现实,不少案件均证明,允许判决的任何一方以各种方式不计代价地抛开法律本身表达所谓自身诉求,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国家机关以特殊对待的方式解决个案,最终造成对其他“遵纪守法”的当事人看上去“严重不公”的结果。这显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