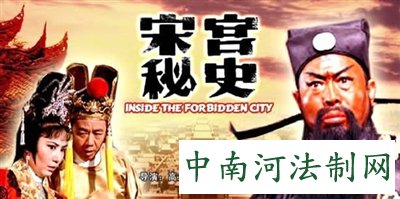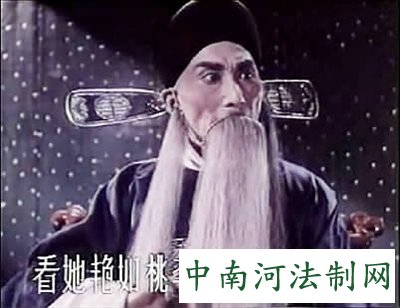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法律图书馆>>法治动态>>法治焦点>>影像中的法律之中国法官篇:司法公正需靠法律而非人格 影像中的法律之中国法官篇:司法公正需靠法律而非人格 2014-9-26 8:37:36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原标题:司法官的人格与个别正义的实现】
电影《宋宫秘史》海报
戏曲电影《十五贯》中的“坏官”过于执 我国法律题材电影中,正义的实现往往依赖于司法官的人格特质而不是法律的力量。我国影片中的司法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清官:包公戏中的包拯、《十五贯》中的况钟等;二是赃官酷吏:《十五贯》中的过于执、《窦娥冤》中的桃杌等;三是现代清官,如《刘巧儿》中的马专员、《法官妈妈》中的女法官等等。这三类司法官员还可以归纳为好官与坏官两种。我国传统题材影视作品中,正义得到伸张,依赖的是包青天这一类主持公道、疾恶如仇的好官;同样的案件,要是碰上过于执这一类贪虐的官员,就没有实现公正的机会。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遇到冤屈,他们总是习惯性盼望青天大老爷出面为自己做主,几乎想不到去改变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糟糕的司法状态。因此,人们追捧着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将自己的愿望和感情投射给他们,却不知明君、贤相、清官、循吏并不像优良、周到的制度那样靠得住。 清官循吏:折射民众对理想司法的期待 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平人物”的概念,扁平人物又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的性格鲜明并始终如一,因此容易识别也容易记忆,人物性格缺乏多面性和复杂性,但能够满足不愿意动脑筋的消遣型读者或者观众的需求,因此长盛不衰,大受欢迎。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的东西,即使阅历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希望看到经久不衰的、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作为逃避现实的寄托,这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睐的原因。” 我国传统法律题材影片中的司法官形象,都是扁平人物,性格单一。正面的,都善恶分明、赏罚公允并散发着一定人格魅力;负面的,都是爱财、酷虐、视百姓为刍狗、视正义如无物之辈。 正面人物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包拯。他性格始终鲜明并且一以贯之,自然是个扁平人物。 胡适称包公为历史上有福之人,“古来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人间,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包公契合了老百姓的传统期待:为官清廉,断案清楚,洗冤惩奸。人们将自己对于司法的期盼寄托于包青天身上,根据包公故事改编的戏曲作品很多,根据戏曲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也不少。京剧电影《铡美案》、评剧电影《秦香莲》以及故事影片《宋宫秘史》等。包公是我国银幕上最多见的司法官形象。 《宋宫秘史》是1965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影片。由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凌波(扮演寇珠)主演。《宋宫秘史》根据脍炙人口的“狸猫换太子”的民间故事改编,开封府尹包拯考察民情,途中遇到一位瞎眼老太太,由此引出一段惊人秘史:二十年前,皇帝的李妃怀有身孕,刘妃闻讯担心李妃生下儿子地位凌驾于自己,便串通太监郭槐用一只狸猫将李妃生下的儿子偷换,还命令侍女寇珠把孩子扔到河里淹死。寇珠不忍下手,焦虑中遇到太监陈林,两人商议将孩子送出宫保护起来。孩子被送到八千岁府上,由八千岁抚养,后来又被刘妃收养并立为太子。李妃因狸猫一事被打入冷宫,十年后被迫离宫流落民间。包公遇上的这位瞎眼的老太太就是李妃。正月十五皇帝观赏花灯之时,包公向皇帝揭露了这段秘史,皇帝令包拯立即调查真相。郭槐虽然被捕入狱,但拒绝认罪。包拯精心策划了一起“夜审郭槐”的戏码,用“阎罗殿”和寇珠的“鬼魂”使郭槐误以为在阎罗殿遭到寇珠索命,惊恐中写下证词,承认狸猫换太子的事实,案件至此真相大白。 历史上的宋仁宗确实是李宸妃所生,也确实由刘皇后抚养,刘皇后还垂帘听政十余年,李宸妃最后病逝于宫中。狸猫换太子及李宸妃流落民间的离奇故事都是虚构出来的。 这部影片中的包公延续其一贯的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人格特质,为李妃的冤屈主持公道,实行正义,让观众感到畅快。不过,包公断案,依现代法治精神和诉讼原则来衡量,自然是谬以千里。他在审讯过程中“频频发动心理攻势,采用疾风骤雨般的发问,穷追猛打,打乱对方的阵脚,抓住对方的破绽,取得案情的突破。”而且为了取得口供,他动辄一声断喝、大刑伺候,为当事人制造心理压力。他还经常用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来收集证据,“夜审郭槐”正是这个套路。张国风叹道:“在包公看来,只要目的纯正、动机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法治”到了今天如何要得? 赃官酷吏:反映民众对司法的认知 传统文艺作品中,除包拯等公案小说的主角外,很多故事中的司法官形象都很糟糕。这些司法官的形象特征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逢迎上司,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卑躬屈膝,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个别官员敢于做些变通,已经是了不得的功绩。如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电影《林冲》中,林冲被设计陷害,误入白虎堂,高俅将其解送开封府,本欲治他死罪,开封府尹知其冤枉,又不能得罪高太尉,判决其刺配沧州。对于开封府尹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了。 二是贪财纳贿。“千里做官只为财”,能够通过受贿发财是官员热衷于执掌权柄的经济动机,贪官罔顾正义,都是受金钱的驱使。戏曲电影《杨三姐告状》中,县长牛成接受高占英家的贿赂,杨三姐在本地自然打不赢官司,只好赶赴天津继续告状。正义一旦被金钱污染,司法公正也就岌岌可危了。 三是武断专横。司法公正不但毁于腐败,也常常毁于司法专横。司法官刚愎自用,往往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戏曲电影《十五贯》中,过于执审理案件,不进行现场勘查,也不听取被告的辩解,主观臆断“看她艳若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据此就判定了苏戍娟和熊友兰杀人劫财。要不是苏州知府况钟复查此案件,苏熊二人就冤沉海底,真正的凶手娄阿鼠倒逍遥法外了。 四是滥施酷刑。古时为了保障承审案件的官员查明事实的能力,赋予其刑讯逼供的权力。该权力一旦被滥用,司法公正就往往被刑杖打得稀烂。传统题材影片中刑讯逼供的场面比比皆是,李翰祥监制、宋存寿导演的故事影片《破晓时分》,就以细腻的表现手法描写山东牟平县一起冤案。案件与《十五贯》情节近似,但以一个第一天到衙门当差的差役眼光来观察这一案件,视角独特。影片展现夹棍、站笼等刑罚,女主角受刑时的镜头切入女子分娩时的惨叫,令人震撼。 五是颟顸无能。“颟顸”乃漫不经心之意,无能指的是缺乏断案水平和掌控案件审理的能力。传统题材电影中昏聩、糊涂、愚昧、庸碌的官员形象不少,大体都属于糊涂马虎、没有本事一类。 法律影片中这些司法官负面形象的特性,体现了文艺作者和一般民众对于司法的认知。人们对于司法的不满,体现为他们在艺术作品中对赃官酷吏加以抨击、挞伐。可惜艺术作品净化官场的作用远不如官场习性力量的强大,政治和司法制度没有根本的变更并走向现代,司法官一代一代颓坏,就是必然的规律了。 实现正义:靠的是司法官的人格力量 我国法律题材影片在法官形象塑造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注重司法官的人格塑造,却缺乏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分析和检讨,一些案件虽然实现了正义,也不过是拜好的司法官人格所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事实、法律和证据的胜利。 我国法律题材电影,往往“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法律的身上”,“如《十五贯》,也是只侧重于县官,没有法律人格化”(梁厚甫语)。遇到好官就柳暗花明,遇到贪官就愁云惨雾。司法之好坏,系于司法官员之人格良莠,法律本身的力量湮没不显。电影《十五贯》提供了司法官人格的对比,案情本来是:尤葫芦在无锡开一家肉铺,生意不佳,向他人借十五贯做进货本钱。尤葫芦酒后跟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是将她卖与他人,十五贯乃其身价。苏戍娟信以为真,当夜便离家出走,路上巧遇客商伙计熊友兰,二人结伴而行。当晚赌徒娄阿鼠进尤家偷窃,被尤葫芦发现便杀人灭口,还盗走了十五贯钱。次日天明,苏戍娟和熊友兰被邻居追上,过于执审理此案,将苏戍娟和熊友兰定为凶手。监斩官苏州知府况钟发现此案可能冤枉,于是向上司请示复查此案,终于案情大白,苏戍娟和熊友兰冤屈得雪,娄阿鼠被绳之以法。此案若一审由况钟断案,不至于错判无辜,幸哉执行时由况钟监斩,否则苏戍娟和熊友兰早已命丧黄泉,哪还有机会得见青天?司法公正与办案官员人格有如此对应关系,真令人感叹命运之偶然与无常。 耐人寻味的是,我国现代题材影视作品仍然注重大力塑造法官的人格,尤其是《法官妈妈》、《南平红荔》这一类主旋律电影,无不将塑造法官而不是法律的现象作为第一位。我国现代司法形象在电影作品中本不多见,一般是以公共政策的需要塑造而成,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电影宣传功能的自觉运用。这些影片质量不差,但仅对司法官人格进行塑造而不在法律制度、证据和案件事实方面多所着力,只怕其行也不远,这是我国当代的电影人需要思考并加以改进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日期:2014-9-26 8:37: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