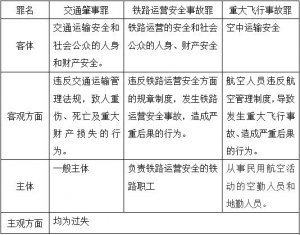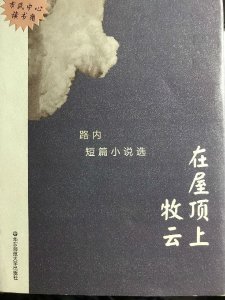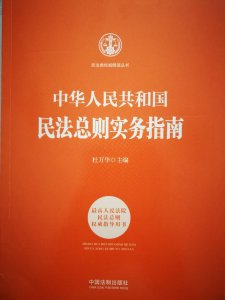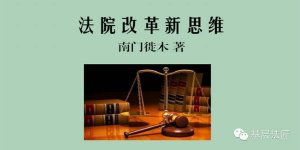|
据何勤华教授回忆,1978年初,整个法学界没有一本法学杂志。50年代创刊、发行的两本法学学术杂志《政法研究》(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编辑)和《法学》(华东政法学院编辑)在1957年、1958年先后停刊后,至1978年初还没有复刊。前者的重新出刊是在1978年底,当年出了一期试刊号,1979年开始正常地出双月刊,名字改为了《法学研究》;《法学》就更晚了,一直到1981年才得以复刊。 记者:回顾中国近30年法学研究的状况,除了法学教材和著作的出版之外,法学论文的发表或许是一个更加普遍、更加重要的领域。何勤华老师,你能否就30年法学杂志的变迁,给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 何勤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北大的《中外法学》,创刊时叫《国外法学》,它是1979年创刊的,而且在改名前主要是刊登译文,与这份杂志相同的,还有一份就是于1978年底恢复重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法学译丛》(前身是《政法译丛》),吉大的《法制与社会发展》,开始时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当代法学》(季刊)。它创刊的时间更晚,已经是80年代中叶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西南政法学院尽管早在1978年夏天就恢复招生了,在司法部五所大学中最早,但它的法学刊物则是在1981年才得以出刊,而且名称也变化了好几次,最早叫《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后来改称《法学季刊》,再后来才改为现在的名称《现代法学》。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在恢复招生时,也都还没有自己的刊物? 何勤华:是的。中国政法大学复校时叫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开始招生,其《北京政法学院学报》是1980年面世的,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后,改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后又改名《政法论坛》。 它的另一份刊物《比较法研究》,创刊要更晚。它是1986年底由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编辑的,后来越办越好,成为法学界的名牌刊物。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律科学》和武汉大学的《法学评论》,创刊也比较晚。 大体上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主要法学刊物的先后面世时间,排列出来应是:《法学研究》和《法学译丛》(1978年底);《国外法学》(1979年);《民主与法制》(华东政法大学创办,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0年);《法学杂志》(北京市法学会编辑,1980年);《法学》(1981年)、《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政治与法律》(1982年);《法学评论》(武汉大学,1983年);《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3年);《河北法学》(1983年);《中国法学》(1984年);《当代法学》(1986年);《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法律学习与研究》(后改名《法学家》,1986年);《比较法研究》(1986年);《山东法学》(后改名《法学论坛》,1986年);《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 到现在,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公开出版的法学刊物也有200余种了,纯学术类的也有50余种了。 记者:法学刊物的变化竟然也这么大。除了法学杂志的数量变化之外,杂志的内容和形式本身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变化呢? 何勤华:应该是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学刊物,一般用的纸张很粗糙,印刷质量也不好,都是小16开,每一期的页码不多,大多数是48页,一年也出不了几期,大部分是季刊,唯一的一份法学月刊就是《法学》。 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法学刊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巨大的进步。除了大部分的刊物改为大16开本之外,页码也大为增加,一般都在128页左右,季刊已经很少看到,大部分是双月刊,月刊也已经增加为三份,即《法学》、《政治与法律》(2008年起)、《法学杂志》(2009年起),刊物所用的纸张也都非常精美。 记者:你所说的很有趣。说到法学刊物的变化,是否还包括了刊物上所刊登论文的变化呢? 何勤华:你提的问题很重要。大体上,早期法学刊物上的论文,一般都比较短,大部分是四五千字的文章,多的也就七八千字,几乎没有一万字以上的论文。但现在刊物上一二万字的论文比比皆是,三四万字、四五万字的论文也不少,前年在《政法论坛》上发表的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论文,竟然达到了17万字! 记者:说到法学刊物,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像无法回避,即在法学刊物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变化的同时,论文的质量是否也跟着在提高呢? 何勤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学术界分歧很大。有的学者认为现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重复的太多,抄来抄去的太多,是在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也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有些论文有重复、抄袭,但主流内容还是针对社会上新出现的法律问题的回应和解答,以及对古今中外法律文明成果的传承和沿续。我是同意第二种观点的。 记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出版社现在每年大量出版法学著作的状况是一样的,您的观点是,不能因为这些著作中有了一些重复和抄袭的内容,就说现在法学著作的出版是在“制造垃圾”? 何勤华:实际上,要求每一本著作都是全新的,既不可能,也同样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人类都是在既定的学术环境中从事研究的,对前人成果的引用、借鉴、发展,当然也包括重述(重复),都是学术活动的内容,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学术发展也是靠一点一滴积累的。 我的观点是,一本著作,一篇论文,如果有10%,甚至5%的创新,就已经很好了,就应当予以肯定。即使同样题目的作品出现了很多,那也不全是坏事,因为它们能面世,就说明社会有这种需求。从世界法学发展史来看,名著的产生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经历了若干时间之后,真正有创新价值的法学著作留传了下来,而大量重复的、乃至抄袭的就被淘汰下去了。 “对西方法学著作的翻译,我们现在已经走在了台湾前面” |